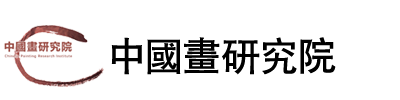田黎明先生
中國文化遵循的是一種自然的文化,即把自己生活、思想之中所遇到的各式各樣的困惑放到自然文化中思考。程顥説:“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我們的先人將自己看成自然中的一體,以儒道釋文化為基礎理念,進行自我梳理、自省與體驗,而這種體驗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知行合一”的方式來實現的。“知”和“行”強調的是“真知”與“必能行”的文化體驗,注重人生經歷、知識結構與心體、自然的圓融,所以中國文化有一種注重宇宙整體性體驗的自覺性。
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講的“知”和“行”與中國畫所提倡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規律相通。而作用的主體,是我們認識事物、超越事物表象的體認方法,進而延伸出“天人合一”、由技進道、由道解物的文化理念。如,先人總結出五行——金、木、水、火、土是對我們日常所見物的概括,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人類日常行為方式。由此,天與人、知與行是可以用“映印”方式來體會的。
田黎明 扎西德勒 纸本设色 180.6×139cm 2000年
中國禪語中有“一月印一切水,一切水映一月”,這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方式,強調用“印”與“映”的方法來把握傳統文化對自然、對社會、對自我的超越和“進境”的方式。“印”是自然本體,“映”是主觀本體,印和映的關係涉及一種意象,其中意象的內結構便是“天人合一”與“知行合一”。如果説,“真知”是印,那麼“必能行”就是映,這可使我們從體驗的意義中來理解王陽明先生“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的內涵。什麼樣的意象才能產生“映”和“、“印”之間的貫通?老子説“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就是這樣的一種理念。若把月作為大文化,水為萬物的象徵,這在中國文化裏強調的便是氣象。月作為一種氣象、一種品格,水作為主體融入其中,才有自己的方位。中國畫特別注重氣象與意象,兩者皆可產生境界。因此,體驗“氣象”與“意象”,其實是體驗境界的問。那麼,在境界中如何來呈現意象呢?慧源法師提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也可以理解為“道”,可以很具體;以“道”來把握萬物,必須有內在規律。所以,我認為在中國畫裏必須通過觀察方法和自己身體力行的體驗,來加強對文化認知的深度和把握。古人所談到的“一”都是經過先人的體驗,我們今天也應該通過這樣的方式體驗它的內在精神。
漢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即是説中國人面對事物的時候要講究行為、講究道理,追尋道而不問其功,這是很重要的中國文化內涵,這個文化理念能夠透徹人的心境。所以説,“明道”是“一即一切”的源頭。唐太宗李世民在《論書》中説:“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這幾句話對於中國畫的載體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提示:指出學習古人書法不只看古人的風格和特點,更重要的是講基礎,這種基礎對於中國畫來講首先便是“作意”。“作意”是立品與取象,而“形勢”指的是一種語言、畫法、筆法。中國文化在這裏對於一種文化的把握,首先是從意境上取象、立格,這對於追究怎麼寫、怎麼畫奠定了基礎。
傳統《六書》歸納出來的六種條例——“指示、象形、形聲、會意、轉註、假借”。其中,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屬於造字之法,即漢字結構的條例;轉註、假借則屬於用字之法。特別是其中的象形、會意,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方式產生了很大影響。比如象形字,“雨”和“月”基本上是按照直觀的方式產生的一種字的形態。“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強調的是觀物成形。對會意而言則是用兩個或幾個物體的圖形組合起來,拼合出字義。這種方法可以把一些無法直接描畫的事、動作、狀態表示出來。比如,三人成“眾”;“北”是兩人相背,物象相融而謙讓等。以象形、會意把握一種觀察方法,在古人意象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東漢蔡希綜在《筆論》中雲:“……凡欲結構字體,未可虛發,皆須象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禾,若山若樹,若雲若霧,縱橫有託,運用合度,可謂之書。”這裏講的便是古人在寫字時一定要有一個“作意”在先,即意象的思維。而以此我們可以引出古人關於竹子的畫法,“一筆片羽、二筆飛燕、五筆驚鴨”等都是從生活中直接觀察並歸納出來的。這個方法首先要取象,要目擊象存;其次便是意合。看到這樣的“作意在先”,對我們來理解傳統繪畫和自己在生活中如何把握對意象的一種體驗方式是至關重要的。照此類推,由畫竹方法再引申出書法中的“永”字八法,永字八法主要是八種力的體驗、八種意象空間的體驗。永字八法之力是借意象空間形成力的方位、歸屬,並由此以技進道,以具體筆力形成筆法,又形成筆意進而上升為一種氣韻,所以謝赫六法第一句是氣韻生動。通過對傳統文化強調的意象方式去體驗用由意生象的結構方式產生境界,對中國畫創作非常有啓發。
周汝昌先生在《永字八法》一書中深入淺出地論述了八法的意象方式。譬如,側(點如側,如鳥之翻然側下),古人用高峯墜石來發力和找形,下筆時強調欲下先上,欲進先退;而策提(仰橫,如鞭策,策馬疾行),啄(由靜而動,強調的是騰凌而速進,如鳥之啄物),這既是一種意象形態,也是一種意象之力。所以永字八法強調的意象,每一種“力”都是意象引出的方法,而這些方法又形成了中國畫的方法。這雖是書法的方式,實際上也是中國畫的方式,解決了中國畫的造型理念。
在書法中,先輩們千變萬化都離不開“體”。這個“體”可歸結為一種心體,書法心體對中國畫的影響,可以借“法”來體驗中國畫的造型法則、用筆法則和氣韻法則。其中,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展開對這些字的體驗;如果去體驗,又是如何在發力當中體現。任何一種筆法都內含有中庸的法則,向內是立道,向外是取象。所以通過書法發力和結構的認識,可以概括有關中國畫創作的一些結構方法,而這些結構方法首先強調的是意象。宋代梅譜總結出一些程式化的經驗,我們通過這種程式化方式,來理解中國畫的特點及其與西方文化在生命體驗、文化取道等方面的不同。西方的人本意識是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反映,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意識則是人與自然圓融的結果。所以中國文化是自然的本色,是對真、善、美的文化體驗。先人把生活中的東西融合到文化中,總結出沖淡、實境、自然、雄渾之氣象,這也是我們在當代中國畫創作中所要學習的。
宋人的梅圖有很多種圖式,而每一幅圖式都有一種境界。畫的雖是梅花,但是在選擇空間的時候,已經把它們作為一個山體,如《燕尾》,花的造型不僅是宏觀的還是微觀的,並通過描繪角度的不同形成意象。又如“雄渾之象”,“具備萬物,橫絕太空”。漢劉邦之詩:“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作為對其體驗的再現,此時的大風、海內、猛士、四方,意在雄渾中產生和諧之勢。而關於“沖淡”,“猶之惠風,荏苒在衣”,使我想起陶潛《歸去來辭》中的“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之句,實是陶公放下形役而內心真正領悟到本然的生命意義,生出“風飄飄而吹衣”之感,不知不覺的光蔭與自然生於內心的明朗。而“實境”則“忽逢幽人,如見道心”,也使我記起朱自清的“朗照”,這是先生心底的光明和中國文人骨氣藉助荷塘產生的文化沉鬱之美,令人感慨萬千。此刻,我感到在他們身上具備的中華文化所倡導的温柔敦厚之美、之德,使他們印映出中國文化的大氣象,體會到真、善、美的載道方式和生命承載的意象空間。體會先人的經典作品之時,是以生命的體驗來參與,此時,古代人發現了這樣的造型,併為這樣的造型確定了立品、取象,像宋人梅譜中“野鶻翻身”“蜻蜓欲立”等,既是以微觀之式來取象,也是對空間的心性所注,達自然天成之境。所以,古人在取象方面解決了如何在自然中把文化的觀照引為物的載體,實現了映印合一的理念,這也正是我們今天所缺少的文化體驗。
對於中國畫意象方面的思考,更多可藉助於古典詩詞加以理解。如秋風,古人寫了很多有關對“秋風”感悟的詩與詞。秋風原是一種自然的形態,借四季如何把自己對社會、對文化的一些認知轉換為自然形態,反映自己心境實為重要,而古人卻是以體道方式來秉承的。秋風可以引申出素風、悽風、高風、涼風、激風、悲風、勁風等各種不同的關於文化深層的體驗。而這些關於風的體驗,實是關於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體驗,而終以自然為上放下小我,迴歸自然來慰藉心靈。如描寫秋景的詩句中,有朗景、澄景、清景;草木裏有衰草、疏木、衰林等,強調的都是主體的一種體驗。
隋煬帝在《悲秋詩》中雲:“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復來;露濃山氣冷,風急蟬聲哀。”悲風——似光陰懷古。又高風,楊師道《初秋夜坐應詔》:“雁聲風處斷,樹影月中寒;爽氣長空淨,高吟覺思寬。”描述一種秋高氣爽而又悲涼之意。這種悲涼通過對自然空曠的描述,把自然空間轉換成心象,並通過意象的方式解決了時間、空間與自然同生而隨人性之生。再如悽風,庾信《晚秋詩》:“日氣斜還冷,雲峯晚更霾;可憐數行雁,點點遠空排。”所繪景是作者心底對自然的點化和濃縮,靠意象的方法來實現的一種經歷與精神轉換。又,莊子雲:“大塊噫氣,其名曰風。”雲氣飄浮,變幻無定,是天地間生生之氣的顯現,莊子以自然宇宙之軀來呼吸,感人至深。
關於勁風,乃人格之立,前面所提劉邦《大風歌》中所指便是勁風。“江海”和“四方”進入到精神本源成為劉邦胸襟和立格的寫照。漢武帝《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通過秋風變化,棲志於心格所向。中國人對字意的理解,以精神之志超越自然之物,又返回自然空間深化自己心性。燕丹子:“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一種悲風不僅道出了“壯士”堅韌的品格,也更能讓人體會到悲風中所藴藏的文化精神。
可以看出,傳統書體強調取象結構和風格結構,實際上是靠意象方式和立格決定的。每個人對自然、生活認知體驗方式之不同,產生了自己獨到而堅定的立格方法和自己所理解的自然空間。由此可見,中國傳統人物畫中所傳承下來的“吳帶當風,曹衣出水”般繪畫樣式,不僅是中國畫線描的一種方法,更是一種審美空間,一種自然形態所映印出的文化空間。“吳帶當風、曹衣出水”與“永字八法”同為一體,無論是其中的風體還是水體,最終都是意象或立格的載體。所以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積澱,由意象思維和表象方式所產生的程式語境,對今天的中國畫創作都有重要啓示。
我們都看過霍去病墓雕塑,它們的精神載體與《大風歌》《秋風辭》也是一體的。因為這種大氣磅礴的精神強調的是寫意、寫胸懷、寫境界、寫氣象,而這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結構。我們讀陶潛的平常心都是日常所見自然平淡的東西,一經文化淘洗,經過個人閲歷和寬闊的精神礪練所產生的自然、天真的心性,才能賦予平常物以境。所以自然之格作為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獨特品性,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載體,我們要通過“天人如一”“知行合一”“印映合一”的體驗方式和人文境界,以温柔敦厚的心體來把握。
關於“象”與“格”,我們可通過一些詩句來體會,進而意識到中國畫的筆墨之跡亦同詩一般,也可以定格在某一層面中來把握人之經歷的不同清音與空回。譬如,畫一張平遠山水,我們可以從中國繪畫史上找出很多關於平遠山水的作品加以參考、借鑑,並通過觀照方式找到對平遠山水的體悟方法,將其定格在文化精神的體驗中,以體驗古人風範來把握畫格。董源的平遠山水、倪雲林的平遠山水、黃公望的平遠山水等,由於各自人生經歷、閲歷等方面的不同使他們觀照對象時所產生的感受也不盡相同,這源於其內所含有的深厚的文化理念和個人體驗;所以董源進入了平淡天真的境界,黃公望進入了平淡寂靜的境界,而倪雲林則進入了平淡空回之境。他們藉助身世,將心底對社會、自然、傳統的體驗方式,在追求品格之時,通過筆墨載體,反映出對文化的體認、對精神的觀照、對自然的品逸,借自然之格來賦予人。又如,魏晉陶淵明的詩和唐代王維的詩,都有一種返璞歸真之境,且寄樂於平常心、平常景。當然,這裏的平常景已不是我們所界定的日常所看到的景,而是已經具有文化象徵的“平常景”,是心性的真體;同樣,平常心也不是我們現在所界定的平平常常的心態,而是進入到一種境界的空間裏。所以陶淵明和王維所看見的平常景、平常心,已是一種心境的體現。
陶淵明在《歸園田居》一詩中所説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特別是後兩句話便是一種追尋本源的思維方式。他寄望籠裏的鳥返林,與樹林中的鳥合一;池塘裏的魚迴歸,與江海的魚合一,來寄託自己內心所。這是他的一種人格意識,強調的是一種返璞歸真的方法——放下所有、回到自然,體現出人的自然境界。而唐王維的詩《闕題二首·山中》:“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則是用印映的感覺把天寒温潤的空間感體現出來。人在自然中的體悟,不受時代的限制,藉助文化空間與人性、心性空間和自然空間來體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文化理念,我們再去體會詩句中的平常心和平常景才更有意義。
王維的許多詩以“空”的感覺把自己的理想境界寫出來。他特有的平常景語概括出這種文化的空間,一直持續了千年。“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這種空的感覺已經不在於物質,而是對心性的生髮,他可以走到某山某水的任一空間都能發現這種感覺,找到這種感覺。因為他的心性是空,具備了精神層面的空靈,當他在自然空間中時便可隨時隨地引發他的境界,而不是一定要找到一種山清水秀的空間。宋人周敦頤(《愛蓮説》)有:“……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也是體現了一種人格的立足,它不受環境的限制,也不受時間和空間的拘禁,所以在這樣的“生有立象”中才有人格風範並生髮出這樣的詩句。嵇康詩:“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於高隅……”單純幾句話把這種氣象傳給了後人,顯示出中國文化的曠達,意象的覓處也在於此。所以我們看書體與畫體、詩體的形式必須要承載意象的方式。
陶淵明詩《歸去來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家園都長滿了荒草,還不趕緊回來,這不是寫實而是寫意,作者面對現實中的任何一個空間,都能夠寫意。此詩描寫出陶公對自己的以往感覺悲哀,覺得耽誤了自己的時光,想到了自己的追尋和目標,覺得前面的路跟昨天比起來仍然寬廣而明朗。他要追求自己心中的境界,這個時候就產生了“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的挺節之境,把“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提升為自己的意氣,找到了自己心境所歸的空間,這個時候眼前的一切物隨着心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使我想到“吳帶當風”,它儼然已成為了一種境界,而不僅僅是一種畫法,形式和內容合為一體。光是內容沒有載體,再好的內容也不能給人以感發和啓迪。陶淵明的詩句雖然寫的都是自己鄉村的生活,但是裏面形式的載體卻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這裏面反映出向內如何思考、向外怎麼汲取的問題,即心性不隨風所動、仍然強調取象與立格作為人之本來闡述的一種單純的形式法則,這與天人合為一體。所以我們對風的體驗、對水的體驗、對山林的體悟或者對某個形式的體驗一定都介入“道”的載體中有感而發,化遭遇為境遇。沒有感受怎麼會產生一種形式呢?形式一定是通過一種感受的方式來決定深度,你能感受的深度決定了形式的深度,所以古人要強調“知行合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非常有道理的,值得我們慢慢體會。
古人的詩,往往以自然之狀來隱喻關於本源的問題。孟浩然的詩表現了一種空曠的感覺,“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不僅給人以空曠的感覺,而且還注入了許多關於人生經歷和遭遇的問題。同樣,王維詩《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我們在讀的時候感受是什麼,體會又是什麼呢?中國古典文化中的許多詩詞,像王維、陶淵明都能夠藉助一定的載體把自己內心所感受或體驗到的東西一一表現出來,而這種載體是中國人心靈深處真、美、善的東西,是中國人心靈最純樸的體現。這種文化理念、這種載體是通過一代代的文人,通過自己坎坷歲月的礪練、磨難才生髮出的。我們的先人、一代代詩人在遇到困境的時候,他自身或者國家遇到困難的時候,仍然把最美好的空間奉獻給後人,這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
南唐後主李煜,作為一代皇帝,他無疑是失敗的,把江山都丟掉了;但是作為一個詩人,他又是偉大的,他把那種喪國之恨轉化成了一種温潤的文化空間,留給了後人。
所以,當我們面對平常心、平常景和非平常心、非平常景時都要認真體驗和思考。尤其是已成為經典的傳統文化,更需要通過我們自己真實的感受來體會。陶公的“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講的是本源的問題。如何把日常的體驗化為一種技能、筆力或筆法,並將其提升為境界,這是我們學中國畫所面臨的一個課題。陳良運論述“詩言志”的規範時引荀子一文:“我感到文須立其所象,立其所品,文質然大道有理法,小道有技能,而不同形式與文思載體之跡將各復歸道。”荀子説:“《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其中,詩與志、書與事、禮與行、樂與和可引為映印中的“境”與“象”。楊成寅著《王羲之》引王羲之《書論》“凡作一字……或如蟲食木葉,或如水中蝌蚪;或如壯士佩劍,或似婦女纖麗”,道出意象很重要的方法,而意象方式又與主題性情相關,感覺一種形象,首先要積累自己很多內在的經驗,然後再通過載體把自己的經驗和閲歷反映出來。我們在筆墨中用筆的方法和用筆的規矩,還有墨法,怎麼“得”,這個得就是先賢倡導的平常心、平常景,不是我們所看到的外表,這是一種心性並能夠被感發與感知。當一種筆法或一種用筆能使我們感受到另外一種聲音、另外一種空間時,一種曾經的美好空間就會被喚起。所以像王維、陶淵明詩句裏對松、石的描述,其形象已經淨化,雖然通過很具體的物,但所闡釋的象卻是“心性”文化,所闡釋的意是人格境界。
今天看古人經典作品,包括看近現代藝術大師作品,他們的人格和藝術是以心性與立象、立格的方式建起敦厚的藝術基礎與文化精神,道理就在其中,但做起來非常艱難。李可染先生講“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就是要下大力氣回到傳統中體驗,同時要在當代的生活中加以自省,自省是屬於心性的文化。中國畫強調自我完善,要自省才能進入到一定境界中,所以有感而發,自然而然的體現是需要渾厚的學養來支撐的。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談到中國文化與生命相關,指出中國的文化理念有一個特點,凡是與自己生命相關的都可以有感而發。但是何為與生命相關?中國文化裏每代詩人之間都映印出人與自然的道心,在文化空間裏,在自己的行程裏找到自己所感悟的東西,如董仲舒所言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曾使多少人為之迴響,但當你真正到了他所描寫的那個荷塘——清華大學裏的那個荷塘,你會發現也不過如此,這個大約300平方米、人工挖出來的荷塘怎能與鄉村的自然荷塘比,但是朱自清先生卻能寫出這樣優美的散文,可見這是由他心裏引發出來的,顯然已超越了眼前的“平常景”。中國文化在他心底積澱的時候已經經歷了獨特的個人體驗,如果沒有這樣的體驗,只能是表層東西,所以,文者見心性,全在心得,而取象、立象、品象是在本心立格的自然中生髮。中國美術史有兩種不同審美理想,以六朝文來比較,芙蓉與雕繢滿眼的文體,一是心性感發,一是緣事而發。
魏晉劉楨《大暑賦》:“其為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為輿達炎燭,靈威參垂步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温泉而沉肌。獸喘氣於玄景,鳥戢翼於高危,農唆捉鱒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温風至而增熱,歊悒懾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這裏似乎缺少了一些意象空間,具體的空間沒有產生意味,所以是緣事而作。
陶淵明《歸園田居》:“……開荒南野際,採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户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則寄予了人類共同嚮往的空間,並以體驗的載體與人的精神、人的心性相關。
當代大學者葉嘉瑩教授在古典詩詞分析論述中曾列舉《玉階怨》三首詩,並由此引出了“實”與“虛”、“具象”與“意象”等課題。其中,虞炎詩:“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思君一嘆息,苦淚應言垂。”偏重於對具象事物的描繪而缺少着意的空間;而謝朓:“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則比較細緻精密,把很細微的感覺寫了出來,但是仍然給人很現實的感覺;而李白詩:“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此月有擬人之覺,所以月雖遠但感覺很近,傳達出一種心象的空間。董其昌畫論有:“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古人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一種精神的觀照成為映印合一的空間,意象便在這種空間裏產生。這個時候,面對現實,怎樣去把握格與象很重要。古人有詩:“淨心抱冰雪”“對酒乃當歌”“茫茫餘落暉”“唯有孤明月”之境,既是一種現實,又非現實,而是一種心體的自然之境,物與我齊一,物通過主體和心性被描述,體驗並上升為對格的觀照與追求。
繪畫一定是反映人所追尋和遵循的一個信仰,並立足於境界,我們通過筆墨載體來弘揚傳統文化精神與時代人文境界,筆墨才能成為一種“氣象”,同時也映印出人在自然中如何鑄煉心性並把握立格、立象的方式,即“一月印一切水,一切水映一月”的體驗方式,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思考和領會的一個重要課題。
摘自《美術教育研究》201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