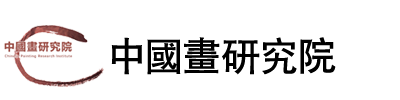青衣仕女 林風眠 紙本設色 66cm×69cm 20世紀60年代 上海美術館藏
中國水墨畫演進的內在理路與文化環境
皮道堅
五十年代以來,真正的水墨現代表達先驅是林風眠(1900年﹣1991年)和關良(1900年﹣1986年)。林風眠主張“中西調合”、畫無所謂中西。他脱胎於瓷畫的光滑、鋭利、輕快的線條,和見筆觸的大面積水墨暈染,證明了水墨語言的轉換產生新意義的可能。關良將水墨的發揮與造型的誇張變形相結合,他選擇以破壞傳統水墨的造型定勢、消解線條的“骨法”功能這一角度,來切入現代表達。石魯(1919年﹣1982年)是一個極其矛盾的人物,他急切地試圖運用水墨話語表達當下真實感受和體驗,像他這樣的藝術家在六十年代可謂罕有。儘管他因為試圖掙脱傳統筆墨的束縛而受到批判,他卻大膽使用一些類似符號的非傳統繪畫語碼,甚至採用油性材料在宣紙上作畫,但終歸未能突破傳統水墨話語的桎梏。
“八五美術新潮”是促使現代水墨性話語成型一個至關重要的階段。“八五美術新潮”不僅提供水墨話語現代轉換的突破口,更通過一些藝術家力圖擺脱舊水墨話語規範的探索,證實了這種轉換的可能。谷文達(1955年生)把西方現代、後現代藝術的觀念性表達方式與中國水墨的表現手段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動因主要受到西方觀念藝術的影響。回頭重新審視傳統、批判傳統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潮。但在谷文達的早期作品中,透過筆墨的精神,仍可看到對傳統的深深迷戀。谷文達的貢獻在於,他的後期水墨作品通過直接使用一些西方化觀念符號,不僅將傳統水墨語言在當下文化語境中的匱乏和疲軟暴露無遺,更提供了水墨話語現代轉換的突破口,而且通過自己的水墨操作,證實這種轉換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以前,谷文達的激進可説是特例。大部分希望擺脱舊水墨話語規範的水墨畫家,實際上還只能在形式技法的層面做些基本的清理工作。這些形形色色、小敲小打的嘗試遊離於當代藝術之外,缺乏對現實的批判精神,也沒有視覺上的力度感,但它們為現代水墨話語作了,推進它在九十年代邁向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雙向發展。
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部分,也是二十世紀末以來中國的重大的變革。中國當代社會現代性結構改變與文化意義上的現代性建設,均與其城市化的進程密切相關。城市化的歷史進程在改變自然景觀的同時,也深刻改變在城市中生活的每一個人,影響他們的思想觀念、道德信仰和交往方式。城市化過程向水墨媒材這一傳統繪畫工具提出深刻的挑戰:涵蓋現實、心理兩個層面的都市空間,是否水墨表達所能切入之處?水墨向以薄、輕、通透、空靈、蒙朧、飄忽取勝,這樣的藝術媒材,能否成為都市激情、力量、速度、時空交錯等等現代感受的真實載體?它能否擔任緊張浮躁、焦慮不安的現代心靈之對應物?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不少藝術家在現代水墨的道路上探索,他們在藝術上的實驗方式,從三方面拓展以都市化為題材的水墨表達空間,完全證實傳統水墨媒材切入當下(涵蓋現實和心理兩個層面的)都市空間的可能性和獨特性。此三方面分別為:
一,藝術家田黎明(1955年生) 、武藝(1966年生)、梁銓(1948年生)等以追憶、尋覓與夢想的方式,表達不可逆轉的現代化進程中,都市人對自然的,以追憶和尋覓民族文化傳統中的精神與人性,並以此延續傳統文化脈絡,表達對現代生活的民族夢想,以質疑所謂普遍的“現代性”(modernity);
二,憑著對當下社會都市人生存狀態的體悟和敏感,或尋求物質世界之象徵對照物的心像風景、或直接介入世紀之交的城市精神圖像,通過變異的造型,大膽的色彩和狂放的筆觸,造成強烈的視覺張力,來表現都市生活中的眾生世相,藝術家如李孝萱(1959年生)、劉慶和(1961年生)、李津(1958年生)、邵戈(1962年生)等均循此方向創作;
三,面對現代化和高科技發展帶來的精神貧困、思想淺薄、急功近利以及因此導致的人性與自然性喪失,謀求水墨繪畫對當代觀念問題的發言權。藉助水墨媒材的隨機性所賦予的想像與自由,以出人意表的水墨圖式語言創造數碼時代水墨文本的神話與寓言,令時代的破碎、貧瘠、荒涼更加觸目驚心。如石果(1953年生)、張羽(1959年生)、劉子建(1963年生)、魏青吉(1971年生)等。
進入新世紀,伴隨著知識界對於全球化的思考,人們開始考察歐洲和美國以外的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不同發展軌跡,反思是否有“另一種現代性” (another modernities)存在,由“實驗水墨”運動引發的、對具有“水墨特質”的視覺語言形式的探索,轉入從文化精神層面深入地對傳統資源重估、評價和利用。中國當代藝術也由此而獲得了新的維度。這新維度已在中國當代藝術近年諸多實踐中充分展現:有利用傳統媒材表達當下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也有將水墨特質、水墨精神和水墨方式植入層出不窮的新藝術媒材,以之作為東方文化精神的新載體,如邱黯雄(1972年生)的水墨動畫《新山海經》。從2010年“第七屆深圳國際水墨展”中的作品 – 包括邱志傑(1969年生)的《兩棵樹》、谷文達的《碑林 – 唐詩後著》、楊福東(1971年生)的《留蘭》、彭薇(1974年生)的《半身寺院夜》、劉俐藴(1974年生)的《山水圖卷》等,亦能十分清晰地把握這一新維度。這些當代藝術作品無論在藝術媒材、藝術理念以及藝術的言説方式上,都有著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的、源遠流長的藝術史文脈,亦有自己極為鮮明的文化特色,並揭示了當下中國新的價值觀和人文精神。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公開亮出“實驗水墨”旗幟的抽象水墨形成一股頗為強勁的勢頭,其共同精神指向反省現代化和高科技發展所帶來的人性和自然性喪失。“實驗水墨”通過創作方法論的轉向,在謀求對當代觀念問題的發言權之同時,也將水墨語言的視覺力度和對現代心靈的衝擊力,擴張至前所未有的程度。九十年代抽像水墨畫家的共同取向,大概是往“極簡”靠攏,而且作品儘量剝離歷史沉積。不過,由於每個畫家的藝術處理各有不同,他們在以上的“共同取向”之外,強調互相徑庭的精神指向,各自融合不同的理念。“實驗水墨”在九十年代的首五年還被視為“異端”,批評界還是為中國畫的前途命運焦慮不安,糾纏於諸如“傳統與現代”、“繼承與創新”、“筆墨中心與非筆墨中心”這些話題上。1996年以後,“實驗水墨”作為最具創造活力的藝術力量,已備受批評界關注,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一個新的“生長點”。抽象水墨在九十年代中後期越來越多見於各種綜合當代藝術的展覽,當初圍繞實驗水墨的種種爭論、躁動與不安也隨之逐漸平息,但這並不意味實驗水墨的文化課題已從基本上解決。
2013年7月14日發佈在雅昌藝術網